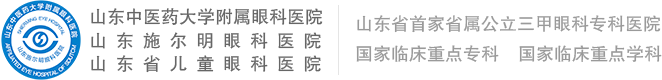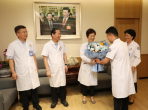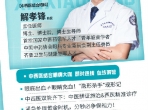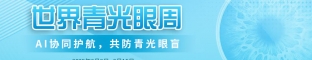齊魯晚報:5枚眼角膜漂洋過海到山東,讓6位病人重見光明
“沒想到眼睛還能有好的一天。”12月15日晚8點半左右,斯里蘭卡捐獻給山東的首批五枚眼角膜,到達山東中醫(yī)藥大學附屬眼科醫(yī)院。早已等待多時的六位患者,連夜接受眼角膜移植手術。首位完成手術的26歲患者劉軍說,本以為要失明了,沒想到還能有機會等到眼角膜。
15日晚8點,來自濟南商河的42歲的孫學蓮,穿著病號服,在病床上瞇著眼睛緊張地等待著還在路上的眼角膜。因為怕光怕風,她眼睛稍微睜開一點都覺得疼。對她來說,更換眼角膜曾是不敢想的一件事,她更沒想到,眼睛還能有完全好的那一天。
早在孫學蓮十歲的時候,就被眼睛紅腫疼痛折磨著。“眼睛里總感覺有沙子,想哭都流不出淚。”上到三年級,因為看不清黑板上的字,再加上小伙伴們總笑她紅眼病,從那時她就輟學在家。
“后來疼得厲害也去看過醫(yī)生,說是淚腺壞死,就一直吃著消炎藥,用補充淚液的眼藥水。”孫學蓮說,眼藥水一天得滴十幾次,眼睛卻越來越睜不開,不要說干點細致的活,就連地里的農活她也做不了。
就在孫學蓮隔壁病房,今年26歲的劉軍,也在緊張又忐忑的心情中,等待著漂洋過海來山東的眼角膜。
十年前,劉軍就開始出現視力模糊,盡管配了眼鏡并進行過激光治療,但還是看不清。“看東西總像隔著霧化玻璃,很想把霧擦干凈,能看清楚眼前的世界。”
在工地上干活的劉軍,一直做鋁合金工作。輾轉多家醫(yī)院看診,最后被診斷為遺傳導致的角膜營養(yǎng)不良——必須更換眼角膜,不然視力會越來越差,以至于最后失明。
接受捐獻后他希望將來捐獻器官
得知角膜移植是唯一的希望,2016年9月,劉軍在同事的陪伴下來到山東中醫(yī)藥大學附屬眼科醫(yī)院,登記角膜移植。不過因為知道眼角膜的稀缺,不一定什么時候能等到的他,一度覺得很灰心。
“就想著帶著妻子出去,要不到各地轉轉,趁著眼睛還能看到,最后再看看這個世界。”劉軍說。而12月初的一個電話,又讓他重新燃起了希望。
“12月8日前后,孩子接到醫(yī)院電話,說是可以移植了,高興得不得了,接著就來住院了。”劉軍的父親劉貴母說,收拾好東西,就從老家鄒城趕來濟南住院,等待角膜移植。
與孫學蓮、劉軍一起等待的,還有另外四名患者。60歲的濟南人郭勝利,40年前曾受外傷;67歲的單縣人姜智金,曾被玉米葉劃傷雙眼;65歲的巨野人高金停,患有邊緣性角膜變性;43歲的棗莊人黃愛君,10年前不慎氨水入眼后視力持續(xù)下降……眼角膜手術,是他們恢復視力的共同希望。
直到15日晚8點半,斯里蘭卡捐助山東的首批眼角膜順利抵達醫(yī)院,劉軍率先做好了手術準備,第一個接受角膜移植手術。15日晚十點左右,經過一個小時的緊張手術,劉軍被推出手術室。
“麻藥還沒退,眼睛暫時沒什么感覺,想到以后就能看清了,很激動也很感謝。”劉軍說,與那些正在等待移植中的人相比,他無疑是幸運的,為了表達這份感謝,他希望將來能把自己身上有用的器官捐獻出去。
捐助角膜先到北京
走綠色通道再到山東
據了解,斯里蘭卡首批捐助的五枚眼角膜,是在12月12日晚抵達北京首都機場的。因為斯里蘭卡沒有直飛山東的航班,所以選擇從離得最近的北京辦理通關。
早在2015年3月,山東省友協(xié)工作組訪問斯里蘭卡期間,就推動山東中醫(yī)藥大學附屬眼科醫(yī)院與斯里蘭卡國際眼庫,就斯方向山東每年捐獻60枚眼角膜、山東向斯方提供醫(yī)療設備的合作項目達成意向。2016年4月,雙方簽署了正式協(xié)議。由于國際間活體捐贈的手續(xù)復雜,在國內相關政策調整,多方推動下,直到今年10月,該項目才完成了在海關、檢驗檢疫機構的報備手續(xù)。12月12日,第一批眼角膜從斯里蘭卡發(fā)出。
山東中醫(yī)藥大學附屬眼科醫(yī)院工作人員寧聰聰,全程負責角膜運回任務。
“12日晚十點左右,搭乘眼角膜的航班降落北京首都機場。眼角膜隨即被儲存到大庫里,等待辦理通關手續(xù)進行提取。”從13日到15日,每天寧聰聰都是不到九點就去海關綜合辦公樓等待,辦理眼角膜的通關手續(xù)。
因為角膜不同于一般物品,保存期有限,角膜通關時特意走了綠色通道。“15日下午四點從大庫取出眼角膜,六點從北京坐高鐵返回濟南,七點五十多到濟南西站,八點半完成角膜運送任務,終于能松一口氣了。”寧聰聰說,因為盒子里有冰塊,要將溫度保持在4攝氏度,剛從冷庫拿出,盒子底部還微微有點涼。
據介紹,在此次受捐的幾位患者中,其中一位角膜邊緣有問題,另一位是眼中央有問題,進行了合理搭配,于是五枚眼角膜得以造福六位患者。
記者還了解到,截止到2016年下半年,斯里蘭卡已累計捐獻了約16萬枚眼角膜。其中,中國是接受捐獻的第二大國,已接受大約6000枚。接受捐獻的地區(qū)包括:北京、深圳、廣東、西安、廈門、河北、成都、天津、內蒙古,山東是第10個受捐地區(qū)。

15日晚8點,來自濟南商河的42歲的孫學蓮,穿著病號服,在病床上瞇著眼睛緊張地等待著還在路上的眼角膜。因為怕光怕風,她眼睛稍微睜開一點都覺得疼。對她來說,更換眼角膜曾是不敢想的一件事,她更沒想到,眼睛還能有完全好的那一天。
早在孫學蓮十歲的時候,就被眼睛紅腫疼痛折磨著。“眼睛里總感覺有沙子,想哭都流不出淚。”上到三年級,因為看不清黑板上的字,再加上小伙伴們總笑她紅眼病,從那時她就輟學在家。
“后來疼得厲害也去看過醫(yī)生,說是淚腺壞死,就一直吃著消炎藥,用補充淚液的眼藥水。”孫學蓮說,眼藥水一天得滴十幾次,眼睛卻越來越睜不開,不要說干點細致的活,就連地里的農活她也做不了。
就在孫學蓮隔壁病房,今年26歲的劉軍,也在緊張又忐忑的心情中,等待著漂洋過海來山東的眼角膜。
十年前,劉軍就開始出現視力模糊,盡管配了眼鏡并進行過激光治療,但還是看不清。“看東西總像隔著霧化玻璃,很想把霧擦干凈,能看清楚眼前的世界。”
在工地上干活的劉軍,一直做鋁合金工作。輾轉多家醫(yī)院看診,最后被診斷為遺傳導致的角膜營養(yǎng)不良——必須更換眼角膜,不然視力會越來越差,以至于最后失明。
接受捐獻后他希望將來捐獻器官
得知角膜移植是唯一的希望,2016年9月,劉軍在同事的陪伴下來到山東中醫(yī)藥大學附屬眼科醫(yī)院,登記角膜移植。不過因為知道眼角膜的稀缺,不一定什么時候能等到的他,一度覺得很灰心。
“就想著帶著妻子出去,要不到各地轉轉,趁著眼睛還能看到,最后再看看這個世界。”劉軍說。而12月初的一個電話,又讓他重新燃起了希望。
“12月8日前后,孩子接到醫(yī)院電話,說是可以移植了,高興得不得了,接著就來住院了。”劉軍的父親劉貴母說,收拾好東西,就從老家鄒城趕來濟南住院,等待角膜移植。
與孫學蓮、劉軍一起等待的,還有另外四名患者。60歲的濟南人郭勝利,40年前曾受外傷;67歲的單縣人姜智金,曾被玉米葉劃傷雙眼;65歲的巨野人高金停,患有邊緣性角膜變性;43歲的棗莊人黃愛君,10年前不慎氨水入眼后視力持續(xù)下降……眼角膜手術,是他們恢復視力的共同希望。
直到15日晚8點半,斯里蘭卡捐助山東的首批眼角膜順利抵達醫(yī)院,劉軍率先做好了手術準備,第一個接受角膜移植手術。15日晚十點左右,經過一個小時的緊張手術,劉軍被推出手術室。
“麻藥還沒退,眼睛暫時沒什么感覺,想到以后就能看清了,很激動也很感謝。”劉軍說,與那些正在等待移植中的人相比,他無疑是幸運的,為了表達這份感謝,他希望將來能把自己身上有用的器官捐獻出去。
捐助角膜先到北京
走綠色通道再到山東
據了解,斯里蘭卡首批捐助的五枚眼角膜,是在12月12日晚抵達北京首都機場的。因為斯里蘭卡沒有直飛山東的航班,所以選擇從離得最近的北京辦理通關。
早在2015年3月,山東省友協(xié)工作組訪問斯里蘭卡期間,就推動山東中醫(yī)藥大學附屬眼科醫(yī)院與斯里蘭卡國際眼庫,就斯方向山東每年捐獻60枚眼角膜、山東向斯方提供醫(yī)療設備的合作項目達成意向。2016年4月,雙方簽署了正式協(xié)議。由于國際間活體捐贈的手續(xù)復雜,在國內相關政策調整,多方推動下,直到今年10月,該項目才完成了在海關、檢驗檢疫機構的報備手續(xù)。12月12日,第一批眼角膜從斯里蘭卡發(fā)出。
山東中醫(yī)藥大學附屬眼科醫(yī)院工作人員寧聰聰,全程負責角膜運回任務。
“12日晚十點左右,搭乘眼角膜的航班降落北京首都機場。眼角膜隨即被儲存到大庫里,等待辦理通關手續(xù)進行提取。”從13日到15日,每天寧聰聰都是不到九點就去海關綜合辦公樓等待,辦理眼角膜的通關手續(xù)。
因為角膜不同于一般物品,保存期有限,角膜通關時特意走了綠色通道。“15日下午四點從大庫取出眼角膜,六點從北京坐高鐵返回濟南,七點五十多到濟南西站,八點半完成角膜運送任務,終于能松一口氣了。”寧聰聰說,因為盒子里有冰塊,要將溫度保持在4攝氏度,剛從冷庫拿出,盒子底部還微微有點涼。
據介紹,在此次受捐的幾位患者中,其中一位角膜邊緣有問題,另一位是眼中央有問題,進行了合理搭配,于是五枚眼角膜得以造福六位患者。
記者還了解到,截止到2016年下半年,斯里蘭卡已累計捐獻了約16萬枚眼角膜。其中,中國是接受捐獻的第二大國,已接受大約6000枚。接受捐獻的地區(qū)包括:北京、深圳、廣東、西安、廈門、河北、成都、天津、內蒙古,山東是第10個受捐地區(qū)。